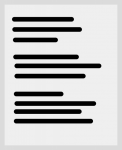在不安的日子里笑出声来
最黑暗的日子里,总要有些最闪亮的希望,才能支撑着人过生活。所以,苏菲没有把爱德华留给她的画像藏起来。她需要曾经的美好提醒自己,未来他们一定会再在一起。

直到有个德国指挥官盯上她。
“我已经很久没跟别人讨论过艺术了。”他对着那幅画像说,但他落在画像上的目光仿佛触摸到了苏菲的身体。
1916年10月,佩罗讷
我梦见好多好吃的。
香脆的法棍面包在烤炉里散发着热气;熟奶酪的边延伸到盘子边上;还有葡萄和梅子,满满地装了好几碗。那些葡萄和梅子的颜色很深,味道很浓,空气里全是它们的香味。
我正要伸手去拿,却被姐姐拦住了。
“走开,”我嘟囔着,“我好饿。”
我要先啃一口那块诱人的奶酪,然后在热面包上厚厚地抹上一层,再抓一颗葡萄送到嘴里。我马上就要尝到那甘甜的味道了。可就在这时,姐姐抓住了我的手腕。
“苏菲,醒醒。”
好吃的慢慢消失,香气渐渐散去。我伸手去抓,它们却像泡沫一样“砰”地一下消失了。
“苏菲。”
“嗯?”
“他们把奥雷利恩抓起来了!”
我侧过身,眨了眨眼。姐姐跟我一样,头上戴着一顶棉帽子,手上端着蜡烛。她脸上仍然毫无血色,微弱的烛光下,两只惊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“他们把奥雷利恩抓起来了!就在楼下。”
我的大脑瞬间清醒。
楼下传来几个男人的叫喊声,他们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,吓得鸡窝里的母鸡一直叫。漆黑的夜,空气里弥漫着恐惧的味道,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我从床上坐起来,裹上睡袍,摸索着把床头柜上的蜡烛点上。
我磕磕绊绊地越过姐姐走到窗边,看着楼下院子里的士兵。刺眼的车灯打在他们身上,还有我弟弟。他两只手抱住头,努力试图避开打在他身上的枪托。
“发生什么事了?”
“他们知道那头猪的事了。”
“什么?”
“肯定是苏埃尔先生举报了我们。我在房间里的时候听见他们喊了。他们说如果奥雷利恩不告诉他们那头猪在哪儿的话,他们就把他带走。”
“他什么也不会说的。”我说。
听到弟弟大叫一声,我们都吓得往后一缩。此刻我几乎认不出姐姐了:24岁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。我知道我脸上惊恐的表情跟她一模一样。这正是我们一直担心的。
“有个指挥官跟他们一起来的。如果被他们找到,”伊莲娜小声说,她一定吓坏了,声音断断续续的,“我们全都会被抓起来,他们会拿我们开刀,杀一儆百。到时候孩子们可怎么办?”
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,但其实根本无法思考。我害怕弟弟可能说出什么。我披上一条披肩,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,偷偷看着外面院子里发生的一切。指挥官的出现说明,这不是几个喝醉的士兵想通过打人来发泄一下那么简单。
我们有麻烦了。他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犯了很严重的罪行。
“他们会找到的,苏菲,用不了几分钟。我们……”伊莲娜因为恐惧提高了音量。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闭上眼睛,随即又睁开。“下楼。”我说,“就说什么都不知道,问他奥雷利恩到底做错了什么。跟他说话,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在他们进屋之前帮我争取点时间。”
“你要做什么?”
我抓住姐姐的胳膊:“快去,但是对他们什么也别说,明白吗?不管他们说什么都不能承认。”
姐姐犹豫了一下,朝走廊跑去,她身后的睡袍狼狈地拖在地上。那几秒钟里,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,恐惧扼住了我的喉咙,整个家庭的命运全都压在我肩上。我冲进父亲的书房,把大书桌的抽屉翻了个遍,把里面的东西——几支旧钢笔、废纸、坏表的零件、老账单——全都抓出来扔到地上,谢天谢地,最后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。然后,我跑下楼,打开地窖的门,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冰冷的石阶。黑暗中,我的步伐异常稳健,甚至可以不必借助摇曳的烛光。我打开后面地窖的门闩,里面的啤酒桶曾经一直堆到屋顶(现在都空了,就像我们的胃)。我把其中一个空桶推到一边,打开那台老铸铁面包炉的门。
我藏起来的小猪崽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。它站起来,从它的稻草床上盯着外面的我,哼哼了一声。我们是在吉拉尔先生的农场被征用时把它救出来的。仿佛是上帝恩赐的礼物一般,它和那些被装上德国人汽车的猪崽们走散了,并迅速地躲进了普瓦兰奶奶厚厚的裙子里。自此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里,我们一直用橡子和剩饭养着它,盼着它能长大点,好让大家都吃上点肉。过去一个月里,“红公鸡”酒吧每个人都在期待享受那脆脆的猪皮、润润的猪肉。
外面又传来弟弟的一声叫喊,接着是姐姐的声音,她说得又快又急,一个德国军官严厉的声音打断了她。小猪的眼睛闪着智慧般看着我,像是它理解我们,并接受自己的命运。
“对不起,小家伙。”我小声说,“但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说着,我向它伸出了手。
回到卧室,我把咪咪叫醒,只跟她说她必须跟我出去但不能说话——前几个月里,这个孩子已经目睹了很多事,所以问都没问就按我说的做了。她抬头看看抱着她小弟弟的我,一只手抓住我的手,迅速滑下床。
冬天来了,外面的空气很冷,傍晚早些时候我们生过火,空气中的烟味还没有散去。透过后面的石拱门,我看到了那个指挥官,犹豫了一下。这个人比起上任指挥官比起来瘦一些,胡子刮得很干净,给人的感觉除了冷漠,还有些智慧。不过,正是智慧,让我觉得更害怕。即使是在黑暗中,我看不清他的脸上。
这位新指挥官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们的窗户,或许是在考虑,这里是不是比那些德国高级军官现在住的傅里叶农场更适合当军营。我怀疑他知道我们这儿的高度足以让他看到整个镇子。这里有马厩,有十个房间,以前我们家是镇上很繁华的旅馆。
伊莲娜倒在鹅卵石道上,张开胳膊护着奥雷利恩。一个德国士兵举起了枪,但那个指挥官抬起手制止了他。
“站起来。”他命令道。伊莲娜踉跄地后退几步,跟他拉开距离。我瞥了一眼,她脸上全是泪水。
咪咪看到她妈妈的时候,我感觉到她抓着我的手紧了紧,我捏捏她的手表示安慰,虽然此时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里。然后我大步走了出去。
“我的天呐,发生了什么事?”我的声音飘进院子里。
指挥官朝我看了一眼,我的语气让他很惊讶:一个年轻女人穿过院子朝他走来,裙边有一个吮着大拇指的小孩,怀里紧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。我的睡帽有点歪了,白色的纯棉睡袍贴在我身上几乎看不出来是件衣服。我祈祷他没有听到我砰砰乱撞的心跳声。
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:“我们犯了什么罪,值得你们这个时候跑来惩罚我们?”
我猜他自从离开故乡后,就没有听到过哪个女人跟他这样说话。院子里突然的沉默让人不由地一惊。
“你是?”
“勒菲弗太太。”
我看得出他在找我的结婚戒指。其实他不必这么麻烦:跟这里的大多数女人一样,我早就把戒指拿去换吃的了。
“太太,我们收到消息,说你们非法饲养牲畜。”
他的法语还算流利,这说明他之前来过占领区;他的声音很平静,说明他不是一个会因为意外而失去方寸的人。
“牲畜?”
“有可靠的消息说,你们在这里养了一头猪。你们应该知道,根据指令,私自扣留政府牲畜是要坐牢的。”
我迎上他的目光。“我很清楚是谁告诉你们这个消息的。是苏埃尔先生,对不对?”因为激动我脸颊绯红,搭在肩上的头发似乎也立了起来,扎的我的脖颈生疼。
指挥官回看他的一个部下,那个部下朝旁边看了一眼,告诉他我说对了。
“指挥官先生,苏埃尔先生每个月至少要来这里两次,他想趁我们丈夫不在的时候说服我们,让我们接受他特别的安慰。因为我们选择拒绝他所谓的善意,所以为了报复我们,他就到处散播谣言,陷害我们。”
“如果消息来源不可靠的话,官方是不会行动的。”
“我想说的是,指挥官先生,你们的这次到访恰恰说明不是这样。”
他看我的眼神令人捉摸不透。
他转身朝房门走去,我跟在他后面,提着裙子磕磕绊绊地努力跟上。我知道,光是这样大胆地跟他说话就是一种罪行了。但是那一刻,我不害怕。
“您看看我们,指挥官先生,我们看起来像是那种天天吃牛肉、烤羊羔或者猪肉片的人吗?”他转过身来,目光闪烁地看着我睡袍下隐约可见的皮包骨头的手腕。光去年一年,我的腰就瘦了两英寸。“我们有因为我们旅馆里丰盛的存货而看起来特别丰满吗?我们原来的二十几只母鸡现在只剩下三只,我们开心地养着这三只母鸡,喂它们吃的,好让你的部下可以来把鸡蛋拿走。而与此同时,我们却过着德国当局所谓节俭的生活——减少肉类和面粉的配额,吃着沙子和麸皮做的面包。那些面包差到没法喂牲口。”
他走到后面的走廊上,脚步声在石板上回响。犹豫了一下,他穿过去走到酒吧间,厉声下了一道命令。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士兵,递给他一盏灯。
“我们没有牛奶喂孩子,孩子们饿得直哭,我们因为缺乏营养都生病了。而你们却大半夜的跑来,吓唬我们两个女人,虐待一个无知的男孩,打我们、威胁我们,就因为你们听到了一个下流人散播的谣言,说我们正在享受大餐?”
我的双手在颤抖。他看到宝宝不舒服地动了动,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因为太紧张,把孩子抱得太紧了。我后退几步,调整了一下披肩,小声地哄了哄宝宝,然后又抬起头来。
我无法掩饰自己声音中的痛苦和愤怒。
“请您进去搜吧,指挥官先生。把我们家翻个底朝天,把那点还没来得及糟蹋的东西全糟蹋完。外面这些屋子也好好搜搜,你的人还没进去看过哪些是他们想要的呢。等你们找着那头神秘的猪,我希望你的部下能好好享用它。”我盯着他的眼睛,比他预想的多盯了一会儿。透过窗户,我能看到姐姐正在用裙子给奥雷利恩擦伤口,试图替他止血。三个德国士兵站在那儿看着他们。
现在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,我看到那个指挥官已经乱了阵脚。他的部下眼睛里透着不安,都在等着他下命令。他可以让他的部下把我们家洗劫一空,然后把我们全都抓起来,以此作为我尝尝无礼的代价。但我知道他在想苏埃尔,想自己是不是真的被误导了。他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喜欢被别人看到自己犯错的人。
以前我和爱德华经常打扑克牌,他曾经笑着说不能跟我当对手,因为我从来不会把真实情绪表露在脸上。现在,我对自己说,一定要牢记:这将是我玩过的最重要的一场游戏。我和那个指挥官对视着,有一瞬间,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静止了:我能听到,远处传来前线隆隆的枪声,姐姐在咳嗽,笼子里那几只可怜的、骨瘦如柴的母鸡在胡乱抓。周围的一切逐渐散去,到最后只剩下我和他,面对着彼此,进行着真相的博弈。
我发誓我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。
“这是什么?”
“什么?”
他把灯举起来,惨白暗黄的灯光下,那幅画被照亮了,那是我们刚结婚时爱德华为我画的。那是结婚的头一年,我又厚又亮的头发披在肩上,皮肤白皙嫩滑,看向画外的目光中透着被爱之人才有的骄傲和沉着。几周前我把这幅画从藏着的地方拿了下来,并且对姐姐说,我才不会让德国人决定我在自己家里该看什么。
他又把灯举高了一点,好看的更清楚。“别把它挂那儿,苏菲”,伊莲娜曾经警告过我,“会惹麻烦的”。
他终于转过身来看着我,看看我的脸,然后又看看那幅画。他的样子好像对那幅画很是恋恋不舍。
“是我丈夫画的。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应该告诉他这个。
或许是因为我正义愤填膺,或许是因为画上的那个女孩跟站在他眼前的这个女人太不一样了,或许是因为站在我脚边这个哭泣的金发孩子。来到占领区两年后,这些指挥官可能也已经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不敬而随意骚扰我们了。
他又盯着那幅画看了一会儿,然后看看自己的脚。
“我想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,太太。我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,但今晚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。”
他看到我脸上几乎毫不掩饰地闪过一丝惊讶,我发现这让他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满足。或许让他知道我原本以为自己死定了就足够了。
这个男人很聪明,而且很敏感。我以后必须得小心了。
“集合。”
他的部下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他的命令,转过身朝外面的汽车走去,车头灯照出他们军装的轮廓。我跟在他身后,一直走到门外才站住。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,是命令司机朝镇上开去。
我们在那里等着,看着那辆军用车重新上路,车头灯照着坑坑洼洼的路面慢慢驶远。伊莲娜开始发抖。她挣扎着站起来,抚在额头上的手的关节发白,眼睛紧紧闭着。奥雷利恩局促地站在我旁边,抓着咪咪的手,为自己像个孩子似的哭而感到尴尬。
我一直等到最后一点汽车引擎声也消失了才开口说:“疼吗,奥雷利恩?”我摸着他的头问。皮肉伤,还有擦伤。什么样的人才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孩子动手?
他缩了一下。“不疼。”他说,“他们没吓到我。”
“我以为他会把你抓起来。”伊莲娜说,“我以为他会把我们全都抓起来。”她这个样子让我觉得害怕:她看上去像是走在深渊边缘,摇摇欲坠。她擦擦眼睛,挤出一丝微笑,蹲下抱了抱她女儿。“这帮德国蠢货,把我们都吓坏了,是不是?妈妈真笨,竟然被吓到了。”
那孩子看着她妈妈,沉默而严肃。有时我会怀疑,我还能不能再看到咪咪的笑容。
“对不起,我现在没事了。”她继续说道,“我们都进去吧。咪咪,我们还有点牛奶,我去给你热热。”她用沾血的睡袍擦了擦手,然后朝我伸出手来,想把小宝宝抱过去。“要不要我来抱小让?”
我开始痉挛似的抖起来,好像我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应该多害怕。我的两条腿软绵绵的,所有的力气似乎都泄到了鹅卵石上。我迫切地想要坐下。“好,”我说,“我想应该给你抱。”
姐姐伸出手来,然后低低地叫了一声。此刻躺在毯子里,被整整齐齐地包裹着,几乎一点儿也没暴露在夜晚的空气中的,正是那头鼻子毛茸茸的粉红色小猪。
“小让还在楼上睡觉。”我说。我连忙伸出一只手撑住墙,好让自己站稳。
奥雷利恩朝伊莲娜身后看看,大家都看着那头小猪。
“我的天呐!”
“它死了没?”
“我给它用了点氯仿。我记得爸爸书房里有一瓶,是他收集蝴蝶标本的时候留下的。我想它应该待会儿就醒了,不过我们得换个地方养它,以防他们什么时候再回来。你们知道,他们肯定会回来的。”
然后奥雷利恩笑了,伊莲娜弯下腰让咪咪看了看那头昏迷的小猪,俩人都笑了。那种难得的、缓缓的、开心的笑。伊莲娜一直在摸它的鼻子,她一只手捂住脸,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手里抱着的就是那头小猪。
“你把这头猪抱到了他们面前?他们跑来这里,你就这样把它抱到了他们鼻子底下?然后你还告诉他们不应该来这儿,让他们走?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可思议。“就在他们的猪鼻子底下,”奥雷利恩突然恢复了一点气势。
“哈!你就在他们的猪鼻子底下抱着它!”我坐在鹅卵石上开始大笑起来。
我一直笑啊笑,直到皮肤开始发冷,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笑,还是在哭。弟弟可能是怕我疯了,拉起我的一只手靠在我身上。他14岁,有时凶猛的像个大男人,很勇猛,有时又像个孩子,需要人安慰。
伊莲娜还陷在沉思中。“要是我早知道……”她说,“你怎么会这么勇敢呢,苏菲?我的小妹妹!是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?我们小时候,你胆子小的跟个老鼠似的。跟老鼠似的!”
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知道答案。
最后,我们终于回到屋子里。伊莲娜忙着用锅子热牛奶,奥雷利恩开始洗自己那张被揍得不像样的可怜的脸,而我则站在那幅画像前。
那个女孩,那个嫁给爱德华的女孩,回眸看着我,她脸上的表情我已经看不懂了。在别人都没有发觉的时候,爱德华早就看穿了我:那画像透着智慧,还有那种对于得失了然自得的笑容。那画里像有一种骄傲。他巴黎的朋友发现他爱上我——一个售货员——时,表示不能理解,而他只是笑笑,因为他早就发现了我身上的这些特质。
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否明白,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他在。